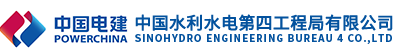泥土里長出的思念,比鋼筋更堅韌——讀《我的母親》有感 |
|
|
|
|
安大爺那篇《我的母親》在屏幕上發(fā)燙時,我正在項目食堂扒拉著午飯。同桌的小伙刷著手機喊:“快看,有個農(nóng)民工寫的文章火了,你快看,比高考作文還動人!” 我嘴里嚼著米飯不以為然,心想多半是媒體又在炒作噱頭。可當指尖劃過那些帶著水泥漬的字句,忽然就想起母親揉面時,面團在掌心發(fā)出窸窣的聲響 —— 原來有些記憶真的像鋼筋里的銹跡,會在某個猝不及防的瞬間,猛地刺透時光的混凝土。 那些沾著灰漿的文字,分明是從三十多年的汗水里撈出來的。每個字都帶著工地上的咸澀,卻把綿長的思念砌成了比任何高樓都堅固的模樣。 最戳心的是那些帶著體溫的細節(jié)。母親端著“死沉鐵鍋”的模樣,讓我突然想起外婆總說的“你媽當年抱著你炒菜,胳膊肘都磨出繭子”。原來天下母親的臂膀都是一樣的,既能扛起生活的重量,又能托住孩子的明天。文中“等孩子吃完餃子自己卻沒吃上”的場景,沒有一句控訴,卻比任何吶喊都更鋒利——它剖開了中國式母親最隱秘的愛:她們永遠把自己放在最后,仿佛那點饑餓與辛勞,會像汗水一樣蒸發(fā)在歲月里。 這位扛水泥的農(nóng)民工,用“墳頭草青黃輪回”的意象,寫出了比許多詩人更動人的時間哲學。當他在工地累得直不起腰時,思念的不是柔軟的床,而是母親“骨子里的硬氣”。這種把苦難嚼碎了咽下的堅韌,不正是中國母親最珍貴的基因嗎?她們從不把苦掛在嘴邊,只是默默把日子過成了韌性十足的麻繩,一頭拴著土地,一頭拴著遠方的孩子。 最震撼的是身份與文字的巨大反差。我們總以為細膩的情感表達屬于書桌前的文人,卻忘了扛著腳手架的肩膀同樣能托舉詩意。當他寫下“三十多年沒叫過媽媽”時,每個字都帶著水泥的顆粒感,卻精準擊中了所有游子的軟肋。這讓我想起在黃龍現(xiàn)場里見過的農(nóng)民工,他們對著手機屏幕抹眼淚的樣子,原來那些不輕易流露的情感,一旦落筆就有千鈞之力。 這篇文章的走紅,根本不是什么“意外”。在這個被算法投喂情感快餐的時代,它像一捧帶著泥土芬芳的野菜,讓我們重新嘗到了真實的味道。原來最好的文字從不需要修辭的包裝,只要裝滿生活的鹽粒與汗水,就能在人心深處生根發(fā)芽。就像作者說的“扛不動水泥就回村躺下”,這份與土地的約定,藏著比任何豪言壯語都更動人。 每當路過工地,總會忍不住望向那些被夕陽拉長的身影。他們粗糙的手掌敲打著鋼筋,沾滿砂漿的指尖也在手機備忘錄里敲打著思念,那些洇著汗?jié)n的文字,正悄悄重塑我們對“詩人”的認知。 原來真正的文學從不在圖書館的精裝典籍里,而在腳手架滴落的汗珠里,在墳頭草榮枯的年輪里,在每個深夜加班者的眼底,在每個為生活奔波者的心房。那些沉默的母親們或許不會提筆書寫,卻用一生的步履,在兒女心上刻下最生動的教義:如何在泥濘里把腰桿挺成標桿,如何在苦日子里嚼出甘飴的滋味。而這,正是那位農(nóng)民工筆下的字字句句,饋贈給這個時代最珍貴的生命教科書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