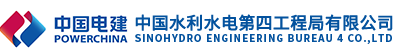筆墨當隨時代 |
|
|
|
|
初入竹壽項目部時,我懷抱著一腔稚嫩的熱忱,踏入了這片喧囂鼎沸的天地。書記為我遞上鋼筆的畫面和鄭重托付的囑言猶在耳邊:“丫頭,好好寫咱們竹壽!”聲音沉穩(wěn)有力,仿佛將整個工地的重量都一并壓在了我肩頭——這紙筆的使命,竟真如鋼筋水泥構(gòu)筑的脊梁一般沉重,壓得人不敢稍有懈怠。 最初的日子,我常常在施工現(xiàn)場的角落里,笨拙地攤開筆記本,在機器的轟鳴與塵埃的飛揚中,捕捉著工人臉上被汗水浸透的紋路。我嘗試描繪工地的脈搏,卻總覺得筆下的文字輕飄飄的,難以承托起眼前這鋼鐵鑄就、汗珠澆灌的巨物。笨拙的筆跡與這沸騰的喧囂世界,始終隔著一層無法穿透的厚障壁。 后來,我漸漸添置了相機,又多了錄音筆,最后連無人機也飛上了工地的天空。那日酷暑難當,烈日灼烤大地,我小心翼翼操縱著無人機升空,遙控器曬得燙手,汗水滴在屏幕上,迸裂成小小的彩虹。透過屏幕俯瞰,深谷間初露崢嶸的壩體如同大地新生的骨骼,工人們的身影渺小如蟻點,卻又倔強地移動著。那鋼鐵之眼所攝取的壯闊風景,是伏案疾書者再怎樣也想象不出的——筆墨的疆域,早被科技開擴得直抵云霄了。 然而,技術(shù)終究只是載體,真正的故事仍在人心里。我鏡頭追逐著工人們的身影,拍下他們黝黑臉龐上綻開的笑容,拍下他們奮力扛起鋼筋時繃緊的臂膀。可每次整理照片,我總下意識篩去那些沾滿泥污、布滿疲憊與皺紋的面孔——似乎唯有“昂揚”才值得定格與頌揚。直到一次偶然翻閱相冊,我猛然驚覺,那些被我悄然刪去的“不完美”,恰恰是工地上最沉甸甸的真實勛章,是汗水、風霜與時間聯(lián)手雕刻的印痕。 一日,我端著相機四處尋訪,看見老工人李師傅正倚在墻根休息。他攤開布滿老繭、裂口縱橫的手掌,仔細端詳著。我屏息按下快門,那雙手便如嶙峋的山石,溝壑里嵌著洗不凈的泥痕與油污。李師傅抬頭見我,有些窘迫地想把手藏起。我走近了,輕聲說:“師傅,您這雙手……真結(jié)實。”他憨厚一笑:“吃飯的家伙嘛,磨粗了不礙事。”——他掌上每一道裂口,都是歲月與鋼鐵無聲對話的刻痕,是生命在粗糲現(xiàn)實里反復磨礪的見證。這雙手的力量與紋路,比任何激昂的標語都更能道出工地的分量。 從此我的鏡頭不再閃避。我不再只尋找笑容,更看見汗水流過黝黑臉頰的溝壑;不再只聚焦偉岸的鋼筋鐵骨,也定格那些倚著水泥管短暫小憩的、沾滿塵土的背影。這些身影里,有年輕的學徒工在傍晚微光下疲憊地揉著肩,有食堂里忙得頭發(fā)蓬亂的阿姐,圍裙上濺滿了油點,卻比工地任何一條橫幅都更顯眼鮮活。 大壩填筑高程達2447.9米那天,人聲鼎沸,旗幟招展,我在攢動的安全帽和震天的歡呼聲中穿梭。透過鏡頭,我猛然看見那位曾被我拍下過雙手的李師傅。他正仰頭凝望著拔地而起的壩體,渾濁的眼中竟閃動著水光,他嘴角微微顫抖著,那淚光映著背后矗立的新壩,便如新壩初升的晨曦映著山川。快門按下的瞬間,我的心房被狠狠撞擊,原來鋼筋水泥的史詩,終由血肉之軀的悲歡血淚鑄就。 工地的喧囂隨工程的推進漸漸沉淀,項目部歸于安靜。隆冬夜晚,窗外寒風呼嘯,我獨坐燈下整理一年影像資料。加濕器輕輕吐出白霧,照片中的汗珠、笑容與號子仿佛重新鮮活流轉(zhuǎn)于眼前。那些刪去又尋回的照片,那些疲憊卻堅韌的影像,終于被我一幀幀仔細選出、印出,鄭重地貼在展板上。 李師傅站在展板前,長久駐足于自己那張手的特寫前,粗糙的手指輕輕摩挲著照片中自己布滿裂口的手掌,良久,嘴角漾出憨厚而復雜的笑意——影像原來不只存留瞬間,更能如醇酒,使勞作與榮光在歲月里彼此認出,愈釀愈深。 此時書記贈我的那支筆,又被我鄭重握在手中。筆桿溫潤依舊,而墨跡早已融入時代的洪流奔騰向前。今日手中筆,既非案頭獨守的孤硯,亦非懸于云端的冰冷機器;它隨金沙江水一同奔涌,流過灼熱汗滴、鋼筋鐵骨、影像光芒,更流向人心深處——時代雖如川流易逝,唯有心與心之間傳遞的光亮,才使那些奔忙的身姿,在歲月沖刷中顯出磐石的分量。 筆管摩挲日久,溫潤如玉;而時代長河喧騰向前,何曾停歇?我們手中之筆,便如那一脈活水,不凝滯于方寸硯臺,不迷失于浮泛云端;它必浸透汗的咸澀、鋼鐵的意志、光影的斑斕——最終,只為替這奔涌向前的壯闊時代,默默刻下普通魂魄那不屈的深度印記。 兩年時光,筆尖已蘸滿了工地的塵土與人聲。我漸漸明白,所謂“當隨時代”的筆墨,并非追逐炫目的浮光掠影,而是要深深俯下身去,傾聽大地深處那些粗糲卻有力的心跳——用鏡頭與文字,謙卑地拓印下汗跡、皺紋與淚光,那才是光陰河床上真正沉淀的金沙,是勞動者為時代刻下的、永不磨滅的碑文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(guān)閉】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