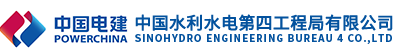一株禾苗里的初心長歌 |
|
|
|
|
傍晚時分,夕陽的余暉輕柔地漫進辦公室,為堆滿文件和電腦的桌面鍍上一層暖橘色的光暈。忙碌了一天的我,終于得以停下手中噼里啪啦敲擊鍵盤的動作,微微靠在椅背上,揉了揉發澀的眼睛。這時,手機屏幕上的新聞標題在柔和的光線中映入眼簾:“山東七旬老人為送特殊禾苗獨自赴京,只為給農業研究添把力”。 新聞中的畫面漸漸在我眼前清晰起來。在沂源縣的河岸邊,宋學禮老人蹲下身洗臉時,幾株模樣特別的禾本植物闖入他的視線。它們不似尋常作物那般依賴肥沃水田,而是在貧瘠的河岸石縫里倔強生長。老人盯著這些植物看了許久,袁隆平院士當年在稻田里尋找野生稻的故事忽然浮現在腦海。他下意識地摸了摸胸前的黨員徽章,轉身回家取了布袋和紙筆,小心翼翼地連根挖出三株禾苗,用河水和濕布保持其濕潤,又手寫了一封介紹信:“這種植物有沒有研究價值?請專家看看。”當老人揣著植株踏上北上的列車時,他或許未曾想到,這株不起眼的禾苗會成為連接兩個時代的“信物”。看著這則新聞,我不禁想起那個反復叩問自己的問題:工作的初心,究竟是什么?自我調任工會工作口后,每天都在處理看似瑣碎的事務,策劃主題活動、為員工送生日祝福……有時,我也會陷入困惑:這些工作,真的能像宋學禮老人的禾苗那樣,孕育出改變世界的力量嗎? 直到去年冬天,我在幫忙整理父親老友的老照片時,一張泛黃的合影吸引了我的目光。1976年,二十幾個青年在龍羊峽水電站工地前站成兩排。他們穿著打補丁的工裝,臉上沾著水泥灰,卻笑得比身后的雪山還燦爛。照片背面寫著:“龍羊峽截流成功紀念,黨員突擊隊留影。”這些面孔大多已退休,但他們的故事仍在流傳。老張師傅曾是龍羊峽的爆破手,為了精確計算炸藥量,三個月用算盤打出上千組數據;李奶奶是當年工地上的“鐵姑娘”,懷孕七個月仍堅持抬鋼筋,孩子出生時體重不足四斤,她卻笑著說:“咱四局人的娃,打小就結實。”這些故事,就像宋學禮老人的禾苗一樣,在平凡中藏著驚人的韌性。他們或許從未想過要改變世界,只是單純地相信,黨員就該沖在最前面。 有一次,和榆林項目團支部書記閑聊時,她興致勃勃地聊起今年團隊深入周邊村鎮開展志愿服務的難忘經歷。他們走進獨居老人的家中,挽起袖子幫老人修理漏水的水管,讓潺潺清水重新順暢流淌;他們耐心地握住老人布滿皺紋的手,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機,讓老人跨越數字鴻溝,感受時代脈搏。一位老奶奶緊緊拉著志愿者的手,眼中閃爍著溫暖的光芒,動情地說:“你們水電四局的孩子……真好哇!就像我自己的親孫兒、親孫女一樣貼心。我年紀大了,好多事兒都弄不明白,要不是你們一趟趟地來幫我,真不知道這日子該咋過喲。你們來了,我這家里都熱鬧起來了,心里也亮堂了,謝謝你們吶!”她說,那一刻,她心中仿佛有道光閃過,瞬間領悟:初心,從來不是那高懸于天際、遙不可及的璀璨星辰,而是悄然落入心田、生根發芽的種子。 辦公室的綠蘿又抽出了新芽,這讓我聯想到新聞里說,科研人員正在對老人送的禾苗進行基因測序。即便它最終被證實只是普通雜草,這份跨越千里的托付本身,已是最動人的詩篇。而我們這些新時代的共產黨員,何嘗不是“初心基因”的傳遞者?當我們在黨員發展會上認真傾聽入黨申請人的心聲,當我們在主題黨日重溫入黨誓詞,當我們在職工困難時遞上一杯熱茶——這些看似微小的舉動,不正是對“為人民服務”最生動的詮釋嗎? 暮色漸濃,我關掉電腦,窗外的城市燈火如星河流淌。宋學禮老人的禾苗此刻或許正在武漢的實驗室里抽芽,而我們的初心,也在日復一日的堅守中悄然生長。它可能不會結出改變世界的果實,卻能讓每個經過它的人,感受到春天的溫度。這,或許就是初心最美好的模樣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